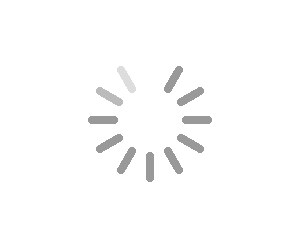数九隆冬的时候,马菊香生下了一个女娃。蔡林忠坐在炕边拨弄女娃蛋清一般细嫩的脸蛋,说快给爸笑一笑,叫爸爸。女娃扑闪开眼睑,露出黑亮的眼睛,果然就咧咧嘴笑了。马菊香幸福地说,她才多大,你就让她叫爸爸?蔡林忠故意犟嘴,说那就叫妈妈,小羊羔落地拜过四方,就会咩咩地叫了。马菊香说,她不是还没拜过四方嘛。所谓拜四方,是小羊羔出生后,挣扎着要站立起来,但体力还太虚弱,四肢也不稳健,就这边跌一下,那边跪一下,跌撞了那么一两圈,小羊羔就会稳稳地蹦跳撒欢了,还会用小脑袋撞着母羊的乳房找奶吃。人们说小羊生下来,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它礼拜四方,是感谢苍天厚土给了它生命呢。
发现女娃是个睁眼瞎是在满月之后。女娃的眼睛长得很漂亮,眼珠黑亮亮水灵灵大葡萄粒一般,眼睫毛也很长,扑闪闪招人喜爱,但大人的手掌在她眼前摆,那眼珠却不会跟着转,只等手掌碰到了她脸蛋上,眼皮才会眨一眨。两口子抱孩子坐火车去过铁路局的大医院,大夫说,这孩子瞳孔晶体天生发育不全,没办法啦。马菊香哭得很伤心,说怎么生了个瞎丫头呀?蔡林忠气得跳脚吼,说我闺女不瞎,我闺女心里亮堂着呢!马菊香说,瞎不瞎也得给她起个名字吧?蔡林忠说,我早起好了,生个丫儿叫明慧,生个小儿就叫慧明。咱们有地有种不愁苗,再生一个就叫慧亮或亮慧。马菊香心里叹息,孩子没等出生,蔡林忠就在琢磨名字了,怎么偏偏选中了一个明字,老天这是有眼还是无眼呀?
明丫两岁那年,国家不再那么困难,上级有了调整政策,要求盲目流动到各地的人口回到家乡去,各企业严格定编定岗,不得再招用临时工人。蔡林忠一次次去找工长,说我要还是光棍一条,说声让我走我就卷行李立马滚蛋,不敢给领导找麻烦。可我有家了,家里还有个累赘孩子呢,可让我带她们娘儿俩去哪儿呀?工长心里喜欢着蔡林忠的为人,一次次地往工务段的领导那儿跑,总算给了一个回话,说那你就先留下吧,工区总还要雇个人烧烧水打打更什么的,你也别怪我不能给你个正经名分,工资福利啥的也不好跟着别人一般齐,等机会吧。蔡林忠连连地点头,说只要不让我走,咋都行,我谢还谢不过来呢,工长是我们一家人的大恩人啊!
铁路上的工作号称五大主要系列,机(机车)车(车站)工(工务)电(电务和信号)辆(车辆),而工务劳作是其中最笨重的,整天日晒雨淋,面对的都是傻大黑粗。有老百姓的顺口溜为证:“上工像逃难的,下工像要饭的,远看是摆弄石头蛋的,近看是流大汗的,上前一打听,原来是工务段的。”其实,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间,蔡林忠从来没有在工区里烧过水打过更,那些活计,工区都是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干,蔡林忠一直是跟着人们去筛道渣,换枕木,夯路基,那都是养路工人最基本也最繁重的劳作,而且他是主力,力气上是主力,技术上也是主力,百分之百的主力。他没怨言,一个不字也不说,他只记着工区给他的好处。开资时,不管给了他多少,他往手心里一攥就走了,回家把那些票子一毛不差地都塞给马菊香。逢年过节了,工务段给工人们分福利,有时是豆油或面粉,那是按人头成桶成袋来的,蔡林忠就只好瞅着了。也有时分带鱼或鸡蛋,工长就在秤头上找公平,留下最后一份,有人喊起蔡林忠的名字,他才跑上前,脸上憨憨地笑,嘴里念叨的是,还有我的呀,谢谢,真是太谢谢啦。人们看着蔡林忠美滋滋离去的背影笑,说这个蔡二呀!北方人称谁为二,有讥其憨钝、不精明的意思,可能是二百五或者二虎头的简约之意吧。马菊香每年从春到秋,一直在山野间忙碌,四处播撒种子,也四处收获果实。但马菊香的田园规整些了,有的在路基下,有的在河套里,还有的在石砬子下,那都是她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,有的地方还是一篓一篓背土垫起的。蔡林忠要帮她在四周围上荆棘,或垒起石墙,马菊香仍不让,她说有那力气不如再扔下几颗种子。蔡林忠说,咱家田里的东西丢的比收的还多呢。马菊香说,那哪是丢?谁顺手掰去两棒包米,摘去一个倭瓜,那是看得上咱们了。
严重的经济困难让国家的政策有了些松动,可以搞些小开荒,农民也可以有点自留地了。路基下的荒地归铁路管,具体的监管部门就是养路工区,工友们吃着蔡林忠带来的粘豆包,都夸蔡家的嫂子真不“菜”,能干!粘豆包用的是大黄米磨的面,大黄米来自马菊香河滩地里的糜子;粘豆包的馅是红豆的,红豆来自马菊香山坡上的疙瘩田。而到了冬天,马菊香就坐在屋子里糊火柴盒,从早糊到晚。邻近的县上有个火柴厂,火车开过来时,捎来了用料,再开回去时,便将整整齐齐的火柴盒捎回去。糊火柴盒有工钱,十个一分,百个一角,马菊香一天能挣一元多,马菊香对此很满足,也很得意,她对蔡林忠说,不少了,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,比起你整天驷马汗流地抡洋镐,我要烧高香了。
临近种地的那段日子,马菊香越发地忙碌起来,她要给村上的生产队剥花生种。马菊香也曾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一起去挣那份工分,女人们手忙着,嘴巴也忙着,忙着说笑,还忙着咀嚼。生产队长一次次进屋吼,偷吃的烂嘴巴!女人们嘻嘻哈哈地反驳,谁偷吃了,你看见啦?生产队长端水进来,喊,敢嘴硬的漱漱口!女人们喝了水,却咕咚咚咽进肚里去,蛙闹塘似的大声喊,谢谢队长关怀,干活还供水喝!只有马菊香平静地含了水,漱了漱,再当着大伙儿的面吐在地上,那水里竟真的不带一丁一点花生的渣屑。那往后,队长就派大车将花生送到马菊香的家里,只让她一人在家剥。来取花生种时,马菊香将一个面盆放在旁边,那里面满是瞎瘪的仁果。队长叹了口气,说这也不能当种子,留给孩子炒炒吃吧。马菊香却执拗地将面盆放在大车上,说我家有,我自己种着呢。
马菊香在山野里劳作,先是把明丫缚在背上,待孩子大些了,就在孩子的腰间拴了一根绳,另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,走到哪儿,就把孩子带到哪儿。那明丫别看眼睛看不见,心里却是亮堂的,到了三四岁,已会帮妈妈干活了。妈妈说红豆,她便将装红豆的袋子撑开;妈妈说黄豆,她再撑另一只袋子,从来不会错的。
明丫五岁的时候,马菊香生下了第二个女儿。襁褓中,蔡林忠的大手在女儿眼前拂动,亮丫的眼珠鼓溜溜地随着他的手转动,蔡林忠做了个鬼脸,亮丫咧咧嘴,响亮地哭起来。蔡林忠哈哈大笑,说这个全须全尾,没毛病!马菊香娇嗔而幸福地捶打他,说不会说话学驴叫,什么全须全尾,咱闺女又不是个蝈蝈!及至发现二女儿耳朵听不见,已是孩子快满周岁的时候了。夫妇俩又抱孩子去了铁路局的医院,医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说这个孩子天生没耳鼓,日后还要哑呢。可能是你们两口子的基因有问题,以后就别生了,生了还可能是个残疾儿。蔡林忠追着医生问,我们两口子都全全科科的,啥毛病也没有呀!医生说,基因组合,非常复杂,我三言两语跟你们说不清楚。听我的话吧,千万不能再生了。马菊香知道问题必是出在自己身上,回家的路上,坐在铁道边呜呜地哭,说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,老天爷这么作贱我!蔡林忠安慰她,说俩闺女,合到一起,就是一个全科人啦,咱们好好养着吧。马菊香说,你就休了我吧,再娶一个给你生。这两个都归我,我不拖累你!蔡林忠跳起脚来吼,放屁!你再敢说这话,我一头钻了火车轱辘!
两个女孩一天天长大了,出落得都很漂亮,两个人形影相随,那也许真是天地的绝配,妹妹听不见说不出,姐姐却音如百灵,说出的话好听,跟着收音机学唱的歌子更好听;姐姐看不见,妹妹的眼睛却如鹰如隼,山里间蹿过一只小兔,高空中飞过一只小鸟,都逃不过她那双明亮的眼睛。小姐俩出门,都是手牵着手的,不知那十指间是一种怎样的交流,该看的该听的该说的,全无耽搁。两人一起去帮妈妈劳作,那亮丫尤其是妈妈的一个好帮手,健硕敏捷得就像一只小鹿,不比别人家的半大小子逊色分毫。
大山里发现了煤矿,另一条铁路横插过来,山坳里的铁路原来是一字,现在就是丁字了。皇妃庵火车站也由昔日的四等小站提升为三等站,站区的线路又增加了两条,矿区里的运煤车要到这里编挂。山窝窝里欢腾起来,因为人们看到了上天赐予的财源。煤车开进来,半大的孩子和家属们围上去,有人攀上火车,将大块的煤炭摔下来,下面的人接应,先还是土篮、麻袋,后来就连手推车也用上了。如果仅仅是供自己家的灶烧还有情可原,有的人家还卖上了煤,引来了远方的大卡车,一吨煤足可顶上铁路员工一个月的工资。车站的领导急了,煤矿上的头头儿也急了,调来了不少警察和保安,可哪管用啊,半大的孩子们惯用麻雀战,一声呼哨,忽地而来,又忽地散去,散去的手里都不空。
那天,马菊香从田里回来,看见灶前堆起了黑亮的煤炭,小姐妹俩则忙着洗手洗脸,将脸盆里的清水洗得黑乎乎。马菊香怔了怔,瞪眼了,喝问:“你们也去偷煤了?”
亮丫拉着明丫的手,明丫说:“不是偷,那么多的人都去了,谁都看得见。”
马菊香吼:“那就是抢!”
亮丫倔强地梗着脖子,明丫说:“煤是国家的,又不是哪个人的!”
马菊香喊:“个人的不能抢,国家的就更不能抢!”
明丫的声音低下来,吭吭哧哧地说:“我们也是……国家的,自己家的煤,别人烧得,我们为什么烧不得?”
马菊香知道明丫说出的话是两人的,妈妈的口型,亮丫看得明明白白。马菊香骂:“胡说八道!你爸挣的血汗钱,你们也敢偷去花,是不是?”
明丫嘟哝说:“妈,这不是一个理儿。”
马菊香说:“怎么不是一个理儿?天下的理就一个,不是咱自己的,拿了就是不仗义!发不义的财,那是亏心,人不报,天报!”
明丫又说:“妈,咱拿回的煤,只自己烧,不卖。连警察都说,只是家里烧,他们就不管了。”
马菊香说:“那不行,不仁不义的事,不能靠着别人管!缺烧的,妈带你们上山拣树枝。”那个年月,铁路上的枕木已换成了水泥枕,工区上早就没有废弃的枕木分给工人当劈柴了。
明丫低声说:“妈,以后我们……不了。”
马菊香说:“光说不不行。这些煤,现在你们就给我送回去!”
亮丫更高地梗起了脑袋。
马菊香问:“我支使不动你们了是不是?”
明丫说:“妈,哪有拿回来再送回去的,不就是几块煤嘛。”
“好,就是几块煤!”马菊香冷笑着,抓起一块碗大的煤块,照着自己的脑门就砸下去,煤碎了,崩溅开,那是黑色的礼花,炸得人心惊肉跳鬼神皆惊。
马菊香又去抓另一块煤,但再不会有黑色的礼花崩炸了,两姐妹扑上去,将母亲死死抱住,明丫哭着喊:“妈,我们听话,妈呀!”
那天,额头上还淌着血迹的马菊香一直跟在姐妹俩后面,眼看着两人背着煤袋子回到装煤的火车旁,又眼看着亮丫扛着袋子,由明丫扶着,一阶一阶攀上车梯,将煤倒回车厢。那一幕,站上的许多员工和警察都看到了,看得人们心潮澎湃感叹不已,人们说,想不到,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呀!蔡林忠死的时候是五十四岁,死状极其惨烈。那年夏天,北方连降暴雨,凶猛的洪水像一条污浊的恶龙,用它的利爪掏毁了很长一段路基。工务段的段长带着精兵猛将赶来筑基救援,铁路局的救援列车也开上来了。修筑被冲毁的路基,必须有大量的山石充填。山石是救援列车从邻近的采石场拉过来的,用机车推送到救援现场。那是雨夜,天地漆黑,就在机车推着另两节装石车挂取已卸空的空车时,两车的挂钩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人们扑过去,在众多手电光的聚焦中,只见两车厢的巨大铁钩正把一个人挤夹在两钩中间,是拦